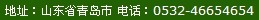|
年夏天,北京的天气格外炎热,十几位装台工人在首都剧场大汗淋漓地埋头工作着。每个人默默地做着自己手上的事:量场地、铺地毯、搭架子、拧螺丝、接电线、调灯光、试音响……时不时地齐声喊道:“一、二、走!”除了喊口号之外,他们之间似乎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交流,每一件事,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默契。“这是自然,同样的活计,我们已经做了上百遍。”技术安装总监米尔基笑着说。自年首演以来,《茶花女》这部改编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上演过很多次,这一次,它终于来到了中国与观众朋友见面。更重要的是,这次是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成立年以来第一次来华演出。 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 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成立于年,是塞尔维亚戏剧历史的一个缩影。建院初期,演出剧目主要来自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的欧洲,诸如法国的莫里哀、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等剧作家的作品都曾被上演,随后还加入了俄罗斯戏剧。20世纪初,塞尔维亚全民的识字率大幅上升,艺术鉴赏水平也大幅提高,本土剧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为了鼓励本国的戏剧发展,当地政府开始举办“贝尔格莱德戏剧艺术节”,这一艺术节后来成为了塞尔维亚戏剧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帮助塞尔维亚本土戏剧在欧洲戏剧中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塞尔维亚王国卷入到了战火当中。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不但无法开展工作,其建筑的主体还遭受了轰炸,受损严重。但在军方的保护和支持下,剧院所有的服装、文件、剧本等材料都被打包,专门送往希腊的科孚岛保存,才躲过了战争的劫难,剧院的历史和传统得以被保存。一战结束后,贝尔格莱德成为了第一南斯拉夫(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首都,三个民族的文艺人士涌到这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有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来到塞尔维亚,不仅带来了戏剧艺术,还带来了芭蕾和歌剧,三种艺术形式同时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上演,于是剧院分别设立了话剧、芭蕾和歌剧三大部门,并延续到了今天。 二战中的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塞尔维亚再次遭到侵略。但是这一次,即使在战况非常激烈的形势下,剧院都没有停止工作,演员们顽强地坚持排练和演出。战争期间,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曾经遭到过两次大规模轰炸,稍微平静之后,演职人员马上进行清理,继续工作,体现出强大的生存意志。二战结束之后,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阶段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塞尔维亚戏剧艺术迎来了黄金时期,作品数量大大增加,剧作家队伍也大幅扩大。得益于铁托的宽松文化政策,艺术创作受到的政治干预较少,因而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荒诞派戏剧、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流派在塞尔维亚轮番盛行,戏剧界出现了新、多、奇、杂的多元化局面,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值得一提的是,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当时为南联盟)时,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是唯一对公众开放的剧院。在长达78天的轰炸中,该剧院仅收一个第纳尔的门票。演出时间也非常特殊,为15:00至18:00,因为在此段时间内,北约会暂停空袭贝尔格莱德。 《茶花女》剧组装台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动荡使塞尔维亚深受打击,但戏剧艺术家们仍在痛苦的时势中坚持创作,保持着澎湃的活力。今天,超过50个实验剧团和先锋剧团遍布贝尔格莱德。而在塞尔维亚全国,有35所专业剧院。这些专业的戏剧机构为戏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今天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已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正式员工约有人,每年约有15个新戏首演,本团演出可达场,另有50场左右的国际剧团演出,吸引着约15万人次的观众。贝尔格莱德是个只有万人口的城市,这样的观众数量可谓是相当可观。艺术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每个艺术家都是人类灵魂的传声筒,他们与生俱来就对艺术有本能的需求——这就是艺术能够保持活力的原因。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经历了多次战争,见证了动荡的历史。历史的沧桑不断地考验着塞尔维亚人民,锻造了他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百折不挠、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剧院这次来华巡演,带来的经典改编剧目《茶花女》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它朴实无华的外表下,是熠熠生辉的戏剧灵魂。 《茶花女》剧作装台 与歌剧《茶花女》气势磅礴的舞台装饰相比,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版本的话剧《茶花女》的舞美可以说是极为朴素。舞台中间只有一组布景:一座巴洛克式剧院的两层包厢。这一简洁的布景却有着双重功效,在叙事上它既交代了玛格丽塔的日常生活境况,在功能上又增加了演员表演的维度,丰富了舞台调度。到了下半场,导演甚至把这样的布景也推入了舞台后方,让演员在空旷的舞台上忘我地翩翩起舞,表演出乡村生活的惬意和爱情的满足。后方的布景始终隐藏在暗淡的灯光里,营造着阴郁不安的感觉。第四幕,玛格丽塔重返巴黎,所有角色悉数出场,登上两层包厢,表演起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场景。随着压迫感极强的音乐节奏,布景再次从舞台后部推出,步步趋近观众,为剧情的推进渲染紧张氛围。舞台上的一切,只是通过简单的变换来实现,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艺术表现可谓别具匠心。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导演尤格·拉迪沃杰维奇解释道:“这一布景是我们剧院内部的复制品。在我们剧院,观众一走进剧场就会发现舞台的布景跟整座剧院几乎是连成一体的。不过这样的感受,搬到别的剧院恐怕就难以呈现了。剩下的只能靠演员。我们的想法是尽量简化舞台上的一切,把一切都交给演员,把一切归还给他们的演技。” 《茶花女》演员排练 于是,巨大的担子落在了十一位演员的肩上。演员们利用精妙的台词、动作设计、肢体语言、面部神情,突破了语言障碍和文化背景,将玛格丽特的勇敢、阿尔芒的单纯、普吕当丝的世故以及瓦尔维勒的下流诠释得惟妙惟肖。所谓无招胜有招,演员直接以舞台行动来实现场景的转换。舞台上没有支点,除了一个大的布景以外,整场运用的是广场式的场景,完全靠演员在舞台上的调度来进行表演。这样的舞台表现手法,正是这次改编的现代性之所在。在看得见的表演的背后,是剧本改编编剧和导演的精心安排。在改编上,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选用的是小说作者小仲马亲自改编的话剧剧本。编剧胡巴奇对原作做了适当的简化,删去了原作中大段的独白,使情节的推进更为流畅,让剧情更为精炼。同时,这样的处理方式,大为拓宽了演员的表演空间,让他们更自由地选择情感的表达方式。这与导演的初衷——把一切归还给演员的演技——同符合契。 《茶花女》剧组谢幕 编排的返璞归真,表演的一气呵成,让观众们感觉仿佛在读一本熟悉的老书。随着舞台上的灯光完全暗下去,玛格丽塔在阿尔芒的怀里死去。最后一幕结束,北京的首演告捷。导演拉迪沃杰维奇激动异常地从观众席里站起来,冲到了后台与演员一一拥抱,他兴奋地叫道:“成功了!观众哭成一片!哭成一片!”北京的夜空忽然降下了倾盆大雨,仿佛在为一百多年前那份痴心情意而哭泣。人类情感是全世界共同的话题,戏剧艺术不分国界,观众的流泪是因为台上两个主人公相爱却无法一起生活下去。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语言、肤色、国籍无关。在塞尔维亚,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爱与恨是所有力量的源泉。人类艺术的历史正是由这两种情感互相交织后推动的,灵感源于人类的爱恨情愁。在编剧胡巴奇看来,要更上一层楼,让经典作品焕发新的光芒,最好的做法莫过于挖掘作品当中的人性。谈论到创作的过程时,编剧胡巴奇坦言道:“在我们现在看来,《茶花女》这个故事也许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到小仲马生活的那个年代看,‘勇气’便是它的关键词。《茶花女》是一部极为勇敢的作品,小仲马是极为勇敢的作者,而故事主人公玛格丽塔是极为勇敢的角色。勇敢的小仲马创作了一个勇敢的女性的故事。在此之前,没有作家试过以妓女作为主角,也没有作家有勇气去挑战世俗观念。另一方面,在故事当中,玛格丽特明知道自己的爱情无法战胜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却依然飞蛾扑火般去追求,最后终于走向了毁灭,牺牲了自己。在我看来,玛格丽特的勇气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人性意义。她的激情,她的牺牲精神,在当今金钱至上的世界中已经很少被人谈及,这些价值观正是我在改编中最想表达的。” 《茶花女》剧组演后合照 勇气,正是塞尔维亚民族从不缺乏的一种精神。纵观历史,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曾经被侵占过40多次,其中有38次被夷为平地,然而,每一次贝尔格莱德都浴火重生,继续发展前行。著名的南斯拉夫当代小说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萨说过:“我们的文学在悲壮的风雨中诞生,它带着我们的文明,在世世代代连续不断的巨大灾难中前进。”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了南斯拉夫文学的性质及其艰难而曲折的发展道路。百折不挠的顽强个性,早已深深植根于南斯拉夫各个民族的灵魂里,塞尔维亚民族也不例外。风雨和灾难,不仅锻造了坚韧的民族性格,还为塞尔维亚的戏剧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和素材。这次来华参加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的作品《茶花女》,很好地代表了塞尔维亚戏剧,它是传统风格艺术品位和现代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代表了塞尔维亚戏剧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创造能力。茶花女的故事虽然在悲剧中结束,但是玛格丽特的精神,却在每一次的改编和演绎中涅磐,不断鼓励人们保持坚强和勇敢。这部作品的主题,恰恰阐释了塞尔维亚戏剧的时代精神:勇于抗争,勇于生存,勇于创新,勇于坚守。 *彭裕超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教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原载于《新剧本》杂志年第五期“穿堂风”栏目 赞赏 长按北京中科白殿疯医院辽宁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
当前位置: 珠海市 >淡极始知花更艳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及茶
时间:2018/7/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竞彩推荐贝尔格莱德游击有望大胜
- 下一篇文章: 彩咖推荐贝尔格莱德红星闪闪,霍芬海姆